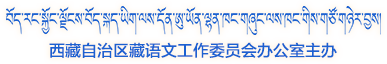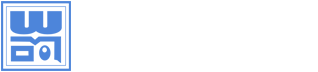试论藏语标准语的定义及其相关问题
��
旺久��西藏自治区编译局译审��
―、课题的提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越发达,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同一民族之间的往来、交流和合作越密切,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问题,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在全国藏区的经济文化事业飞速向前发展,交通更加便利,人员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由于没有一种在所有藏区通用的藏语标准语,这不但给个人生活带来诸多困难和麻烦,而且给社会交往和信息化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因此,研究确立一种在所有藏族聚居区能够通用的藏语标准语,这是广大藏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和迫切要求,是一切致力于藏语文事业的专家学者和藏语文工作者的多年追求,是一项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确立藏语标准语,对于贯彻党和国家新时期民族语文的方针政策,统一和规范藏语,消除藏族内部的语言障碍,实现藏语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准确无误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和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增进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发藏族,尤其是开发那些只懂一种语言的藏族群众的智力,促进藏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地向前发展,构建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藏语标准语的定义问题:研究确立藏语标准语,关键的问题,是要提出一个精确的藏语标准语的定义,这是藏语标准语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藏语标准语的根本方针问题,是开展藏语标准语工作的前提条件。藏语标准语定义的准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藏语标准语的发展方向和具体操作问题。对此,作为我个人观点,提出如下藏语标准语的定义,愿与各藏区专家学者切磋。��笔者认为,确定藏语标准语,具体地说,就是要确定藏语的文法标准、基础词语的标准和语标准。因此,藏语标准语的定义,应该是:以藏文为依据,以卫藏地区的藏语为基础,以拉萨语音作为标准音的白话文式的藏语标准语。��
三、以藏文为依据的理由:��
(一)理论观点:按照马克思语言学的观点,自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最初是人类的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语言。当语言发展到相当程度时,便产生了文字。文字的基础是语言,语言的科学性规律是文字。也可以说文字是语言的代替物,是语音的符号,又是语言的载体。文字产生于人类的语言,但是,一旦有了科学的、有规律性的文字,人类的语言活动,就必须受文字规则的约束,也就是必须以语言文字规律,去指导和规范人类的语言活动。这是一条基本的原理。��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藏文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创制,至今毫无争论地在整个藏区,乃至于不丹、锡金等国家和地区统一使用的文字。藏文属于拼音文字。它有着丰富的语音和语义表达能力,能清楚地转达世界上几乎所有语种所要表达的信息。藏文与其它文字不同的是,它有《三十颂》和《音势论》这两部严整的发音和文法理论著作。一千多年来,这两部著作作为藏语文的基本文法规则一直沿用至今。今天,我们讨论确定藏语标准语,做的就是人类语言活动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也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藏文规则的约束和指导。也就是说,我们的藏语标准语,必须以传统的藏文文法理论《三十论》和《音势论》作为基本的文法规则。��
(二)著名学者的观点:近代藏族著名学者根敦群培在《白史》中说“应知从初创藏文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其间,藏文的名词与字形,并无大的改变。即现在凡是曾学藏文的人,观看古藏王时的碑文等,也仍能粗知其文义。西藏特别是从宗喀巴大师时起,到处盛行刻印经书。西藏现在所有的大量书籍雕版,在这地球上,据说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从刻版时起,直到现在,其字形与文法等同一法度,一点也没有变更。由此可知,如果我们任何时候都以这些经典著作的名词及文言为标准,那么,无论经历多长时间,西藏的语言,当然永远保持统一。譬如一部用文言写的书,上自阿里,下至安多,无论拿到哪里,都能会读,懂意思。”��著名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东嘎・洛桑赤列文集》中的文章《有关发展藏语文方面的初步想法》里,在谈到藏文的几个与其他民族的文字不同的特点时说:“藏文是根据藏族聚居地的大部分人普遍使用的语言(ཕལ་ད་)创制的,因而具有普遍性。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藏文,在最初创制时,不是按当时当地的方言(ལ་ད་),而是按大部分地区都能听懂的语言创制的。因此,藏文是卫藏地区、康区、青海、甘肃、云南、锡金、不丹、印度等国内外所有藏族聚居区的共同文字,除了用各地方言(ལ་ད་)写的外,只要是按标准语的藏语(ཕལ་ད་)写的,都能理解其内容”。��著名藏学家恰白・次登平措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西藏教育》第四期上,在谈到文化教育和新闻宣传部门的任何文字资料,在不违反藏文传统文法和正字学的前提下,所用语言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应作为一件大事来推进的同时,说:“另一方面,近来在一些已经和正在出版发行的藏文报纸和刊物上发表的藏文小说、民间故事、歌词集等,不知是想让某一地方的群众易懂,还是随便按当地的方言土语写的,里面所使用的语言,尽是一些没有文法与正字学根据的方言,使广大藏族看不懂其内容。如果这种现象,任其泛滥下去,最后的结果,在所有藏区统一使用的藏文文法和正字学会分崩离析,藏区语言只能跟着各种方言走,致使上下南北四分五裂,互相不通语言,藏文的声明论、正字学、文法、辞书等成为无根无据的东西,民族的传统文化会被毁得连个名字都不剩,无法进行抢救,其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星火燎林(་ག་ས་ནགས་་བག་པ་)的长远后果,要认真思考,更要预防”。��
(三)笔者观点:从以上专家学者所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尽管在一千三百年期间,不少藏文学者著书立说,对藏文的某些方面提出过改革设想,藏文本身也经历过三次较大的规范,但是藏文字形、语法结构等的统一性根本没有发生变化。相反的,经过三次规范后,藏文变得更加统一和完整,逐渐形成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超方言的藏文书面语。特别是从十五世纪起,藏文的印刷术得到广泛发展以来,藏文文法和字形基本上被锁定在一个标准线上,藏文著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更趋于规范和统一。来自不同方言区的藏族学者们,用藏文书面语著录而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对弘扬藏民族的文化起了重大作用。那时出版的诸多藏文著作中的词句,被誉为藏语文的典范,至今为后人传颂和运用。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随便把一部用藏文写的著作,带到藏区的任何一个角落,用当地的语音读给人听,就是一个不懂藏文,只懂藏语的人,也能听懂其基本内容。相反的,如果拿出一本不是以藏文为依据,而是完全照某地的方言土语写的书读给他听,那他肯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倒头来,你还得用有文字根据的藏语来向他作解释。由此可见,藏文是藏语的书面形式,书面藏语已成为藏族人民通用的共同语。藏文书面语不是藏语的简单拼写,书写藏文书面语还要讲究藏文正字法。否则,语言中就会发生同音异义的现象,就不能准确地表达词语的本意。藏语中的许多名词,虽然读音基本相同(古时读音也不相同)但其构成字母的不同,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例如:藏文名词中的“ཐབས་”是“办法”之意,“འཐབ་”是“斗争”之意,“ཐབ་”是“灶”之意,三个名词读音基本相同,但意思完全不同。又例如:藏文中的“ཀ་”是“柱子”之意,“་”是“水渠”之意,“་”是“苦味”之意,三个名词读音相同,但意思全然不同。这就是藏文书面语为何要强调讲究正字法的原故。如果不遵循藏文文法,不讲究正字法,其结果,藏族的共同语言会支离破碎,藏文与各种方言土语之间无法沟通,有文字依据的所有藏区都能听懂的藏语书面语,反而成为只是在书面上所载的语言,久而久之,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也都会变成谁也看不懂的一堆废纸。这是我们提出藏语标准语必须以藏文为依据的主要理由。
四、以卫藏语作为基础方言的理由:我们说藏语标准语必须以藏文为依据,并不是说不应以某个地方语作为基础语,相反的,我们必须以某一个地方语作为基础语。这是因为没有一种由地域、人口、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构成的某地方语作基础,就不可能形成一种能够广泛推广使用的共同语,我们的藏语标准语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我们提出藏语标准语,要以卫藏语作为基础语。这里,首先要明确卫藏的地域范围。卫藏的大概念,是指前藏和后藏两地,这个地域范围是很广的。但是,作为藏语标准语基础语来源的卫藏,主要是指拉萨和日喀则、江孜地区。��
卫藏语成为藏语标准语的基础语,主要是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卫藏两地,特别是拉萨,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拿卫来说,自松赞干布迁都拉萨以来,先后由十一个赞布在拉萨施政,其中从赞布赤松德赞开始,在拉萨地区对藏文进行过三次较大的规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丹颇章地方政权一直到1959年,拉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所在地,由这里向西藏各地发出藏文公文、布告等,可以说是藏文行文最集中的地方;西藏三座最大的寺庙、藏医学院等也都在拉萨,是西藏文化及宗教的中心。拿藏来说,萨迦政权和藏巴汗期间,日喀则地区曾一度成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四世班禅起,直到民改,西藏最大的寺院之一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一直是西藏另一个势力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藏文使用较集中的地方。卫藏两地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相对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牢固,文化底蕴丰厚,群众语言丰富多彩。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拉萨一直是西藏首府,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藏人员、交通、旅游,商贸的汇集处,是西藏最发达的地方,是人们想往的圣地。日喀则是全区县最多,人口最多的地区;日喀则市是西藏第二大城市,是后藏地区的中心。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交际工具,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不但会发生内涵的变化:而且会发生外延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和建设,卫藏两地的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卫藏语也随之获得了极大丰富和发展。卫藏语,作为藏语标准语的基础语,应是大势所趋,众口一辞的事情。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作为基础语的卫藏语中不应包括没有藏文根据的方言土语。例如:在拉萨语中“ང་པ་”叫;“ང་ག་”,“ལག་པ་”叫“ལག་ག་”;在日喀则语中“ང་པ་”叫“་བ་”,“ལག་པ་”叫“ལག་་”。还有在卫藏语中,有时丢掉原有表示原因的虚词བས་ར་གས་等不用,却用拉萨方言“ཙང་”来代替等。对于这些缺乏文字根据的卫藏词语和一些“时髦”语言,目前不应给什么“合法席位”。可以这样说,凡是有藏文根据的词语,不管出自哪个藏区,都应视为藏语标准语的成份而吸纳和运用;凡是没有藏文根据的词语,哪怕其来自藏语基础语的卫藏,也不能作为藏语标准语的成份而使用。��
五、以拉萨语音作为标准音的理由:确定藏语标准语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藏语的语音问题。目前造成的方言差别,决不是藏文本身问题,而是各地对藏文的发音不同而造成的。因此,语音标准不确定,就永远也形成不了共同语。签于拉萨语音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提出以拉萨语音作为藏语标准语的标准音。这里,首先要确定拉萨语音的范畴。作为藏语标准语的标准音,我认为主要是指拉萨市城关区这一范围的语音。拉萨语音应是吐米桑布扎创制藏文时所依据的主要语音之一,也是对藏文进行三次规范的主要根据之一。可以说,拉萨语音比较符合藏文典范声明论和正字学的发音规划。经过漫长的演奕,如今天拉萨语音在整体上变得比较轻柔,典雅,已成为各地藏族群众容易学习和掌握的语音。我们不防拿拉萨语音与多康地区语音作个比较:拉萨语中读་་་་ 四个元音字母时,字音分得很清楚,但在康区和་似乎读成一种音,因此在康区一些会藏文,但藏文正字法没掌握好的人,往往把元音符号ཞབས་་和་་写错。例如,有的把绿松石的ག་写成ད་,把数字བ་ག་写成བ་ག་,把叔叔ཨ་་写成ཨ་་,把数字二十写成་་等。这些都是因为把་和་读成一个音造成的。在卫藏语中三十个声母的读音分得很清楚。例如:在卫藏语中ཀ་和ག་,ཏ་和ད་ པ་和བ་,ཞ་和ཤ་的读音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在多康地区的读音中却分得不清楚。在安多地区读་字时,上齿贴下唇发音,结果发出来的音成了“发”,几乎听不出是བ་音,但把པ་字的音却读成བ་字,因此,把པཎ་ན་读成བན་ན་,把པད་མ་འང་གནས་读成བད་མ་འང་གནས་另外ཞ་和ཤ་读音也分得不明显。以上举的例子是一些单音字的读音区别。在拼读一些有元音字母的音节,例如:ང་和ཞང་ལགས་和གས་བ་和བ་等时,在拉萨语音中分得很清楚,但在多康地区则不然。当然,拉萨语音也并非完美无缺,在拉萨语音中因受拉萨方言的影响,不符合藏文音读法的残损音也不少。一些应读出来的音在拉萨语音中却不读。例如:字母པ་ཕ་和བ་的下加字ར་在拉萨语音中不读。因此,把ང་་读成ང་་,把་་读成ཕ་་把ན་་读成ན་་还有一些音节的下加字也不读。例如,把ན་读成ན་等。又例如:藏文阴性字母ད་ཛ་等,在拉萨读音中,往往读成重音,如把ད་ག་རང་读作་ག་རང་,把ཛ་ག་读作་ག་。对上述字母,如果加前加字或上加字,就应该作重音,但却读成轻音,如把ད་་读成་་ 把་དག་་读成་དག་་,总之存在着轻重读音相错的问题。这些读音毛病,必须通过学校的藏文教学和各种宣传媒体进行统一规范,以纠正读音差别,统一藏文读音。��
我们把拉萨语音作为藏语标准语的标准音的另一个原因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的。目前我们的广播、电视、电影、对外宣传、各种文艺节目、会议用语等,主要使用的是拉萨语音。这就等于实际上,拉萨语音作为标准音已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学习和使用拉萨语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时尚和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也没必要试图用另一种地方语音代替拉萨语音,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把拉萨语音推广到更大的语音范围,使其成为全藏区的语音标准,促进藏语标准语的更快形成和发展。��
六、藏语标准语运用藏文应以白话文为主的理由:凡有一定的藏文水平的人都清楚,藏语方言(ལ་ད་)与白话文藏语(ཕལ་ད་)之间,白语文藏语与藏语文言(ས་ད་)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方言一般是只有该方言区的人才能听懂的语言,主要使用于方言区内部;藏语白话文是更加通俗化了的藏文书面语,主要用于新闻宣传、文艺演出、会议用语等各种大众化的语言活动中,而文言文主要用于经书、旧式公文、文学作品等中。白话文直接与口语相联系,通俗易懂,容易为全民中的多数所掌握;而文言文具有词汇优美,语言精练的特点,一般不易为全民中的多数所掌握和运用。当然,这种差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能认为藏语中存在着三种毫无相关的语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藏文书面语是被规范了的藏语方言,而藏语方言是变了音的藏文书面语、藏文书面语和各地方言之间有一套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我们仔细分析一些方言词语,就能从其语音和语义上分辨出它是从一个统一的语言中演变出来的痕迹。例如,拉萨方言中的问语“ང་ངས་” “འག་གས་”等,是书面语中的“ང་ངམ་” “འག་གམ་”等的后加字“མ་”字的音读轻了以后变成了“ངས་”又例如,“་་འ་ནས་ན་ང་ང་”是书面语中的“་”字的音读快了以后变成了“ང་”。类似从书面语演变成为方言的例子举不胜数。我们的责任是尽量要让方言接近文字,提倡语言文字化,而不应该提倡文字言音化。我们强调藏语标准语,必须以藏文为依据,但是这并不是说不要语言大众化、口语化。推广和普及藏语标准语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他们掌握和使用藏语标准语时,才能形成全社会的共同语。因此,我们的藏语标准语所要运用的藏文应以白话文为主,语言要尽量做到大众化、口语化,通俗易懂,这样,便于学习掌握和推广运用。��
七、结论:综上所述藏语文的历史沿革、发展区域、语音特点、使用现状等诸多因素,藏语标准语的定义,确定为以藏文为依据,以卫藏地区的藏语为基础,以拉萨语音作为标准音的白话文藏语标准语,我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也是能够实施的。��
八、推广普及藏语标准语的主要途经:随着藏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交通的更加便捷,人员来往和相互交流的日益密切,藏语标准语定义的确定和实施,是历史必由之路。为了使今后的藏语标准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就丰富发展和推广普及藏语标准语的途径问题,谈几点初步想法:藏语标准语的确立和推广普及工作,最终是一项政府职能行为。要真正做到普遍使用藏语标准语,就要做大量的群众社会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机构来组织实施不行。因此,应由藏语标准语诞生地西藏自治区牵头,成立五省区藏语标准语协调推广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在五省区协调推广藏语标准语工作;��
(一)学校教育的作用:藏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的藏文教材的编译工作同推广使用藏语标准语紧密结合起来。首先,作为藏族学生主课的藏文课中,把教授藏文标准音的读法,学习有关藏文古籍、现代藏文、藏文文法等作为重要内容,当作学习藏语标准语的根本,认真组织教学。同时,有教学条件的学校,要把已译成藏文的数理化课程、作为丰富和发展藏文标准语的重要途径,认真进行教授;��
(二)媒体的作用:藏语广播电视电影、信息网站、各种文艺节目、书刊报纸、图书资料、对外宣传媒体等同时要承担统一和规范语言的责任,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大力推广和普及藏语标准语,为规范和统一藏语标准语,推广和使用藏语标准语,发挥出各自的作用;��(三)翻译的作用:翻译,是藏语标准语增添新的语汇,获得新鲜血液的重要途径。通过翻译,把国内外各类学科的主要著作译成藏文,又通过翻译,把新涌现出来的新闻术语译成藏文,并经过五省区专家学者规范审定后,由藏语标准语权威机构发布,在五省区统一使用,对于丰富发展和规范藏语标准语中的新词术语,定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责编:豆格才让�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