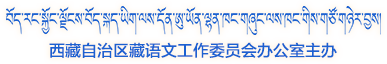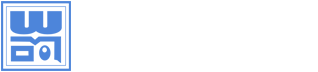琼氏部落东迁对嘉绒地区的文化影响
punctuation'>
摘要 琼氏部落从西部象雄迁徙至东部嘉绒以后,在嘉绒藏族文化的发展和流变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文章从琼氏部落东迁对嘉绒历史地名产生的影响,琼鸟信仰在嘉绒地区的演变,琼氏后裔与苯教在嘉绒的传播,东西“女国”的历史文化联系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琼氏部落东迁
对嘉绒藏族文化带来的新的变化和影响。
关键词 象雄;琼氏;嘉绒;苯教
藏族史上琼氏部落东迁近年来得到诸多学者对其历史文化成因及其年代问题的探讨。作为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直接结果之一,古象雄的苯教文化也传到了嘉绒地区,对嘉绒的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其中几个重要的方面来探讨琼氏东迁对嘉绒地区的文化影响。
一、历史地名中的象雄文化遗存
在嘉绒地区,明显带有古象雄文化内容的地名并不多,但少数的几个地名所包含的内容却具有浓厚的象雄文化内涵。首先,位于甘孜州丹巴县的墨尔多神山,其藏文全名是“嘉姆墨尔多雍仲邦泽”(![]()
![]() 。“嘉姆”指的是起源于古象雄的苯教女性护法神“斯贝嘉姆”;“墨”也常常音译为“穆”,是苯教祖师顿巴辛绕米沃且的姓氏,因此在苯教文献中常常引申为神圣的意思;“多”为岩石或石山;“雍仲”是苯教的重要符号�d;“邦”是叠的意思;“泽”是山峰的意思,连起来就是“用雍仲重叠的斯贝嘉姆的神圣山峰”。作为嘉绒女性保护神的斯贝嘉姆是在佛教没有传入吐蕃之前青藏高原最具普遍性的保护神之一,如今仍然是嘉绒地区最大的保护神。根据《墨尔多神山志》[1],墨尔多神山的殊胜之一就是从墨尔多神山仰首可见冈底斯山的山顶;俯首可览八条蜿蜒飘逸的河流,这些河流是献给冈底斯山的哈达。表现了在早期象雄文化中被称为“山王”的冈底斯神山的神圣地位,以及墨尔多神山与冈底斯山在青藏高原早期神山信仰系统中的文化一体性。
。“嘉姆”指的是起源于古象雄的苯教女性护法神“斯贝嘉姆”;“墨”也常常音译为“穆”,是苯教祖师顿巴辛绕米沃且的姓氏,因此在苯教文献中常常引申为神圣的意思;“多”为岩石或石山;“雍仲”是苯教的重要符号�d;“邦”是叠的意思;“泽”是山峰的意思,连起来就是“用雍仲重叠的斯贝嘉姆的神圣山峰”。作为嘉绒女性保护神的斯贝嘉姆是在佛教没有传入吐蕃之前青藏高原最具普遍性的保护神之一,如今仍然是嘉绒地区最大的保护神。根据《墨尔多神山志》[1],墨尔多神山的殊胜之一就是从墨尔多神山仰首可见冈底斯山的山顶;俯首可览八条蜿蜒飘逸的河流,这些河流是献给冈底斯山的哈达。表现了在早期象雄文化中被称为“山王”的冈底斯神山的神圣地位,以及墨尔多神山与冈底斯山在青藏高原早期神山信仰系统中的文化一体性。
“嘉绒”是另一个重要的地名,藏文全名为“嘉姆擦瓦绒”(![]() )①也有更为详细的名称,描述为“
)①也有更为详细的名称,描述为“![]() ”,意为“嘉绒十八大平地”或“
”,意为“嘉绒十八大平地”或“![]() ”,即“嘉绒十八大峡谷”。《琼普王统・白琉璃之镜》记载的十八大雪分别为纳雪(
”,即“嘉绒十八大峡谷”。《琼普王统・白琉璃之镜》记载的十八大雪分别为纳雪(![]() )、索雪(
)、索雪(![]() )、吉雪(
)、吉雪(![]() )、苏木雪(
)、苏木雪(![]() )、噶尔雪
)、噶尔雪![]() 、玛尔雪(
、玛尔雪(![]() )、尼雪(
)、尼雪(![]() )、达雪(
)、达雪(![]() )、杰雪(
)、杰雪(![]() )、玉雪(
)、玉雪(![]() )、麦雪(
)、麦雪(![]() )、甲雪(
)、甲雪(![]() )、达合雪
)、达合雪![]() 、雪(
、雪(![]() )、达布雪(
)、达布雪(![]() )、玛雪(
)、玛雪(![]() )、支雪(
)、支雪(![]() )、尼合雪(
)、尼合雪(![]() )、姚合雪(
)、姚合雪(![]() )。也称“夏嘉姆擦瓦绒”
)。也称“夏嘉姆擦瓦绒”![]() ,简称为“嘉绒”。汉文历史文献中出现过很多种译法,如嘉绒、嘉良夷、呷弄、甲戎、甲冗、甲摩绒、察瓦绒、甲莫察瓦绒、查可、甲莫峨溪、冉�、革勒、垄巴等[2]。尽管汉文史籍对嘉绒的地名来源和族群识别方面有众多的解释,但是,“嘉绒”一词的最初词源为藏文则是毫无疑问的。“夏嘉姆擦瓦绒”中,“夏”意为“东方”;“嘉姆”意指苯教护法神“斯贝嘉姆”
,简称为“嘉绒”。汉文历史文献中出现过很多种译法,如嘉绒、嘉良夷、呷弄、甲戎、甲冗、甲摩绒、察瓦绒、甲莫察瓦绒、查可、甲莫峨溪、冉�、革勒、垄巴等[2]。尽管汉文史籍对嘉绒的地名来源和族群识别方面有众多的解释,但是,“嘉绒”一词的最初词源为藏文则是毫无疑问的。“夏嘉姆擦瓦绒”中,“夏”意为“东方”;“嘉姆”意指苯教护法神“斯贝嘉姆”![]() ;“擦瓦”,意为是“炎热”;“绒”,意为“峡谷”,全称意为“女神斯贝嘉姆保护下的东方炎热的峡谷”,简称“嘉绒”。对于“嘉绒”这个历史地名的解读,毛尔盖・桑木旦和格勒等已经作过详细的论述[3],本文不再赘述。嘉绒位于“四川省西北边陲之地,具体说是云南、贵州、甘肃、青海与四川省结合部的大渡河、金沙江、岷江和黄河源头部分地区”。按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嘉绒的地理范围或嘉绒藏族具体分布区主要为:四川省阿坝州和甘孜州境内的马尔康县、壤塘县、理县、汶川县、黑水县、金川县、小金县和丹巴县的全部和红原县、泸定县、康定县、雅江县、道孚县、炉霍县、新龙县和雅安地区的宝兴县、天全县、石棉县的部分地区构成。其中,马尔康县、金川县、小金县是嘉绒地区的腹心地带。
;“擦瓦”,意为是“炎热”;“绒”,意为“峡谷”,全称意为“女神斯贝嘉姆保护下的东方炎热的峡谷”,简称“嘉绒”。对于“嘉绒”这个历史地名的解读,毛尔盖・桑木旦和格勒等已经作过详细的论述[3],本文不再赘述。嘉绒位于“四川省西北边陲之地,具体说是云南、贵州、甘肃、青海与四川省结合部的大渡河、金沙江、岷江和黄河源头部分地区”。按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嘉绒的地理范围或嘉绒藏族具体分布区主要为:四川省阿坝州和甘孜州境内的马尔康县、壤塘县、理县、汶川县、黑水县、金川县、小金县和丹巴县的全部和红原县、泸定县、康定县、雅江县、道孚县、炉霍县、新龙县和雅安地区的宝兴县、天全县、石棉县的部分地区构成。其中,马尔康县、金川县、小金县是嘉绒地区的腹心地带。
“勒乌”是嘉绒核心地带金川县的一个地名,当地一个乡的名字就冠以“勒乌”,称作勒乌乡。“勒乌”为象雄语“李卫尔”(![]() )的音译,意为“王”或“风之王”。民间流传,古代象雄王曾派出一位名叫勒乌的大臣至东方的嘉绒地方,并在此建立一官寨,其原址位于今金川土司官寨所在地。因此,那位古象雄王派来的大臣的名字后来就成为了当地的地名。
)的音译,意为“王”或“风之王”。民间流传,古代象雄王曾派出一位名叫勒乌的大臣至东方的嘉绒地方,并在此建立一官寨,其原址位于今金川土司官寨所在地。因此,那位古象雄王派来的大臣的名字后来就成为了当地的地名。
二、琼鸟信仰在嘉绒的传播
在嘉绒地区原有的斯巴苯教的基础上,琼氏家族的东迁带来了以琼鸟信仰为主的象雄西部的苯教信仰传统。琼鸟不仅是琼氏家族的祖先图腾,作为琼鸟本身也经历了从琼鸟-神鸟-琼神的演变过程。早期的琼鸟,与琼氏部落的巨鸟信仰有关,据传琼部落的祖先是从一巨鸟卵里孵化出来并繁衍生息的。因为祖先崇拜,致使琼鸟逐渐演变成了神鸟,人们赋予它许多超乎寻常的神性。这些神性导致这个神鸟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变为一个神即琼神。此时,虽然它仍是一巨鸟形象,但其本质上已演变成了一神�o。随着琼神信仰的出现,开始有了许多与修行琼神有关的文献和修行人。一些被认为是修行琼神得道的法师,在琼氏家族中享有崇高的声望。随着琼神修行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外氏族人也开始修行琼神,从而原本与琼氏家族祖先有关的神,逐渐变成了青藏高原上具有普遍性的一神�o。
在藏族原始信仰中,琼神还有一个与鲁(�D།)神相克的关系,这在苯教信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传统的苯教信仰中,琼神是鲁神的克星,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与鲁神有关的疾病等,可通过修行琼神医治。在嘉绒地区,琼神早已不是只有琼氏家族的后裔才供奉和修行的神�o,而是整个嘉绒藏族共同供奉和修行的神�o,也是嘉绒地区具有共性的文化符号。我们在嘉绒地区的许多文献、壁画、宗教仪式以及舞蹈等民俗文化中处处都可见到琼鸟形象,这个神�o及其信仰是随琼氏部落东迁而传至嘉绒地区的。
琼氏家族东迁至嘉绒地区,带来了苯教和琼鸟崇拜文化,嘉绒地区因地理原因而形成和保持了古代苯教的许多特点,没有完全被佛教化。而位于西藏西部的琼氏家族发源地,因佛教的传入和渗透,古苯教文化远没有嘉绒地区传统和纯粹。过去嘉绒诸土司部族,普遍认为自己是琼氏后裔,巴底、巴旺和革什杂土司的族源,也与琼氏部族有关。当地文化中具有浓厚的琼神信仰色彩,在嘉绒地区土司官衙大门多有雕画的琼鸟,历史古地名中也经常出现带有“琼”字的名称,例如“琼日”“琼溪”“琼波”“琼洼”等,相传是琼鸟降临之地或琼鸟停歇之山,而且这些地方的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象雄或者西藏琼波丁青等地。
琼氏部落是嘉绒地区族源结构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琼氏史籍《琼波王统・白琉璃之镜》在讲述吐蕃的地理疆域时,除了上部阿里三围(![]()
![]() )、中卫藏四翼(
)、中卫藏四翼(![]() )和下多康六岗(
)和下多康六岗(![]() )以外,还提到了八部荣喀(
)以外,还提到了八部荣喀(![]() )、十八雪(
)、十八雪(![]() )、八约勤(
)、八约勤(![]() ),这些指的正是嘉绒地区。上述史籍中记述了一段与琼鸟有关的美丽传说:
),这些指的正是嘉绒地区。上述史籍中记述了一段与琼鸟有关的美丽传说:
从苯教神祗贡桑辛拉(![]() )的心部发出一束深红色光,射入穆氏(
)的心部发出一束深红色光,射入穆氏(![]() )国王夫妇身上。由七束光组成的露珠里,生出六子,其中长子被一箭距离的白色光芒环绕,被称为穆王秋杰尔轩(
)国王夫妇身上。由七束光组成的露珠里,生出六子,其中长子被一箭距离的白色光芒环绕,被称为穆王秋杰尔轩(![]() ),住在穆日木波(
),住在穆日木波(![]() )山上。他与女神贡扎玛(
)山上。他与女神贡扎玛(![]() )生有一子,被称为穆夏尔(
)生有一子,被称为穆夏尔(![]() ),即穆钦沃巴尔玛(
),即穆钦沃巴尔玛(![]()
![]() )。他与恰王汤波(
)。他与恰王汤波(![]() )之女恰坚拉准(
)之女恰坚拉准(![]() )结合后生四卵,从中孵化出琼氏四子,分别为南喀当之琼(
)结合后生四卵,从中孵化出琼氏四子,分别为南喀当之琼(![]() )、扎波基堆之琼(
)、扎波基堆之琼(![]() )、塞弥坚之琼(
)、塞弥坚之琼(![]()
![]() )何扎穆日坚之琼(
)何扎穆日坚之琼(![]() )。四子依父命到各地教化众生。其中,幼子穆日扎(
)。四子依父命到各地教化众生。其中,幼子穆日扎(![]() )之琼鸟最初降落在象雄卡佑地方,后再次腾空而起,降落在嘉日祖丹(
)之琼鸟最初降落在象雄卡佑地方,后再次腾空而起,降落在嘉日祖丹(![]() )①嘉日祖丹,位于今西藏阿里地区冈底斯山以西约100千米处,是非常著名的苯教圣地。因据说古代琼鸟降落在此地而成为了苯教徒膜拜的地方,同时也是苯教大师的修行地。之地,这个地方也就被称为琼隆。之后与天界喀拉度莫(
)①嘉日祖丹,位于今西藏阿里地区冈底斯山以西约100千米处,是非常著名的苯教圣地。因据说古代琼鸟降落在此地而成为了苯教徒膜拜的地方,同时也是苯教大师的修行地。之地,这个地方也就被称为琼隆。之后与天界喀拉度莫(![]() )生下白、黄、蓝和花四个卵。其中,从花卵中孵化出的琼帕岔莫(
)生下白、黄、蓝和花四个卵。其中,从花卵中孵化出的琼帕岔莫(![]() )被派往多康及其边缘地区教化众生。琼帕岔莫在前往多康地区的途中,短暂降落在一个有六座山峰的山上,这座山就是琼布孜珠山(
)被派往多康及其边缘地区教化众生。琼帕岔莫在前往多康地区的途中,短暂降落在一个有六座山峰的山上,这座山就是琼布孜珠山(![]() )②孜珠,意思就是六个山峰。此山位于今西藏昌都地区丁青县境内,为苯教非常著名的圣地,有著名的苯教寺庙孜珠寺。在传统的地理概念中,此地区被称为琼波丁青,意思就是琼鸟后裔琼氏部落聚集的地方。此地是琼氏部落东迁过程中的一个缓冲地带,因此有许多琼氏部落后裔仍然留在此地,繁衍至今,而且建有很多苯教寺庙。琼帕岔莫与强玛女神(
)②孜珠,意思就是六个山峰。此山位于今西藏昌都地区丁青县境内,为苯教非常著名的圣地,有著名的苯教寺庙孜珠寺。在传统的地理概念中,此地区被称为琼波丁青,意思就是琼鸟后裔琼氏部落聚集的地方。此地是琼氏部落东迁过程中的一个缓冲地带,因此有许多琼氏部落后裔仍然留在此地,繁衍至今,而且建有很多苯教寺庙。琼帕岔莫与强玛女神(![]() )化身的一女子生出白、黄、蓝、花四个卵,从白卵里孵化出拉塞噶茹(
)化身的一女子生出白、黄、蓝、花四个卵,从白卵里孵化出拉塞噶茹(![]()
![]() ),黄卵里孵化出拉塞赛尔佐(
),黄卵里孵化出拉塞赛尔佐(![]() ),蓝卵里孵化出拉塞纳茹(
),蓝卵里孵化出拉塞纳茹(![]() ),花卵里孵化出琼普岔沃(
),花卵里孵化出琼普岔沃(![]() )。其中,琼普岔沃被派往绒康(
)。其中,琼普岔沃被派往绒康(![]() )即峡谷地区教化众生。他先来到了洛察瓦绒(
)即峡谷地区教化众生。他先来到了洛察瓦绒(![]() ),即今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之后又去往布波尔岗(
),即今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之后又去往布波尔岗(![]() )和孜达(
)和孜达(![]() )地区。在孜达地方,与一天资聪慧的女子结合生有一子,名为齐吾塞(
)地区。在孜达地方,与一天资聪慧的女子结合生有一子,名为齐吾塞(![]() )。齐吾塞长期居住在布波尔岗,降服了察瓦绒、玛尔岗(
)。齐吾塞长期居住在布波尔岗,降服了察瓦绒、玛尔岗(![]() )、志岗(
)、志岗(![]() )等地的诸多罗刹恶魔,古拉玉泽(
)等地的诸多罗刹恶魔,古拉玉泽(![]() )和卡瓦格博(
)和卡瓦格博(![]() )、岗布日(
)、岗布日(![]() )等神山承诺保护苯教和传播苯教。之后,到达阿尼玛卿山脚,最后达到东嘉绒,有墨尔多山神拉年旺秀(
)等神山承诺保护苯教和传播苯教。之后,到达阿尼玛卿山脚,最后达到东嘉绒,有墨尔多山神拉年旺秀(![]()
![]() )和他的一百多名随从纵马相迎。他到达墨尔多神山的地点,被称为琼郭(
)和他的一百多名随从纵马相迎。他到达墨尔多神山的地点,被称为琼郭(![]() )。从此,琼氏部落的后裔以及苯教在嘉绒地区扎下了根。
)。从此,琼氏部落的后裔以及苯教在嘉绒地区扎下了根。
《琼波王统・白琉璃之镜》是一部成书年代较晚的藏文史籍,且上述所记也难成历史事实,然这一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琼氏部族东迁和苯教文化东传的一些线索。文中所涉猎之历史地名,如:琼波丁青、嘉绒等今天仍是苯教文化区,这也说明了传说与史实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嘉绒藏族史志》根据当地文史资料说:“第八代藏王止贡赞普时期,有个名叫穹帕茶莫的人来到嘉绒地区,在现今金川流域传教,后来被嘉绒地区最大的本教寺院雍忠拉顶(即后来的广法寺)寺尊为该寺的始祖”[6]。
琼氏部落未到达嘉绒地区之前,嘉绒地区已经有传统的原始苯教信仰,墨尔多神山是当地的主要保护神。而琼氏部落东迁并传入苯教后,使当地的苯教文化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这对后世当地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2年,马长寿先生在嘉绒地区调研时发现:“凡嘉戎土司之门额俱雕有大鹏式的琼鸟。形状:鸟首、人身、兽爪,额有二角,鸟啄,背张二翼,耸立欲飞”[7]。尽管他所持“此鸟本为西藏佛教徒所崇拜”的学术观点值得商榷,但是,马氏文中“奉供最虔者则为嘉戎。吾常于涂禹山土署见一木雕琼鸟高三尺余,在一屋中供养,视同祖宗”的记述则反映了嘉绒地区盛行琼鸟崇拜的文化现象。
三、琼氏后裔与苯教在嘉绒的传播
嘉绒地区的苯教信仰,应该是在藏族原始苯教信仰的基础上,与从象雄西部传入的雍仲苯教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嘉绒地区独特的苯教信仰文化。当时“嘉绒地区不仅有当地土著居民,而且他们早已信仰苯教,墨尔多等神山早已成为当地信徒的保护神”[8]。在雍仲苯教从西藏西部,即象雄地区传到嘉绒地区的历史进程中,琼氏部落或家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强化了当地的苯教信仰。他们既是传播雍仲苯教的使者,又是嘉绒地区诸多部落的祖先。嘉绒地区的大部分土司,特别是绰斯甲、促浸、赞拉等土司均信仰苯教。民间流传:“大金川流域嘉莫绒地区的十八土司之一绰斯甲宗,约在三家土司的曾祖科潘(![]() )之后,出了绰窝斯甲(
)之后,出了绰窝斯甲(![]() )土司,他在这里建造宫室,其后裔称为绰斯甲。这个家族中出了许多苯教的证悟者和绰窝坚赞土司(
)土司,他在这里建造宫室,其后裔称为绰斯甲。这个家族中出了许多苯教的证悟者和绰窝坚赞土司(![]() )、象嘉・更噶诺布(
)、象嘉・更噶诺布(![]() )等”[9]。
)等”[9]。
金川县的勒乌摩崖石刻是一个苯教母续传统的圣地,在苯教传统中,母续传统是一个被认为是来自古象雄的修行传统。目前,在勒乌摩崖石刻中能看到的线性石刻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苯教母续八大畏惧寒林、密宗和大圆满传承诸上师,以及苯教日常念诵咒文。苯教母续八大畏惧寒林是母续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中的八个重要修行道场;苯教传统中的密宗和大圆满被认为是来自古象雄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象雄大圆满被认为是藏族先民创造的极其殊胜的修行传统;许多日常念诵的经文也是用象雄文撰写的。不仅如此,摩崖石刻中出现了李西达仁大师的线刻图像,其题记为:“幻术无边女性变成男,李西达仁通晓大圆满”①该题记的藏文原文为![]() 。虽然摩崖石刻是14至16世纪之间刻成的,但其内容提到的大圆满却是指古象雄的大圆满传统,李西达仁与苯教大圆满的重要文献《大圆满央泽隆乾》教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联系,所以,题记中说他精通大圆满,是指这个教法及其传承。[10]古象雄文化在嘉绒地区的传播活动,琼氏后裔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带到了嘉绒,而且在嘉绒地区进行了长期的传播,这些被认为是来自古象雄的苯教文化内容在嘉绒地区的传播,极大地丰富了嘉绒地区原有的原始苯教内容,强化了青藏高原东部的嘉绒与西部的象雄之间的文化联系。
。虽然摩崖石刻是14至16世纪之间刻成的,但其内容提到的大圆满却是指古象雄的大圆满传统,李西达仁与苯教大圆满的重要文献《大圆满央泽隆乾》教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联系,所以,题记中说他精通大圆满,是指这个教法及其传承。[10]古象雄文化在嘉绒地区的传播活动,琼氏后裔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带到了嘉绒,而且在嘉绒地区进行了长期的传播,这些被认为是来自古象雄的苯教文化内容在嘉绒地区的传播,极大地丰富了嘉绒地区原有的原始苯教内容,强化了青藏高原东部的嘉绒与西部的象雄之间的文化联系。
嘉绒地区历史上最重要的苯教寺院莫属雍仲拉顶寺(![]() )。该寺位于阿坝州金川县安宁乡,距墨尔多神山有九十多千米,位于距金川县促浸镇南33千米处的金沙江东岸。许多文献都提到了这个寺院以及其在嘉绒地区的历史地位,但雍仲拉顶寺的前身,就是一处苯教早期的祭坛或苯教师们的修行处。许多苯教寺院都有这样的演变历史,从俗人修行地逐渐演变为僧人寺院,例如青海省贵德县的琼毛寺和甘肃省夏河县的佐海寺等都是由塞康(
)。该寺位于阿坝州金川县安宁乡,距墨尔多神山有九十多千米,位于距金川县促浸镇南33千米处的金沙江东岸。许多文献都提到了这个寺院以及其在嘉绒地区的历史地位,但雍仲拉顶寺的前身,就是一处苯教早期的祭坛或苯教师们的修行处。许多苯教寺院都有这样的演变历史,从俗人修行地逐渐演变为僧人寺院,例如青海省贵德县的琼毛寺和甘肃省夏河县的佐海寺等都是由塞康(![]() )演变而来的,也体现了僧人寺院传统对俗家修行传统的深刻影响。公元8世纪,赞普赤松德赞灭苯之时,卫藏地区的许多塞康被毁,许多苯教大师逃到了多康地区。从上述墨尔多神山的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一部分苯教大师逃到嘉绒地区,并把卫藏地区的塞康文化带到了此地。这些塞康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被改变为寺院。雍仲拉顶寺曾是嘉绒地区最大的寺院之一,是整个嘉绒十八土司的总寺院,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统领作用。雍仲拉顶寺在金川战役中被毁之后,嘉绒地区许多苯教寺庙都跟雍仲拉顶寺一样被强行改宗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另外一个较为重要的苯教寺庙就是金川县的昌都寺(
)演变而来的,也体现了僧人寺院传统对俗家修行传统的深刻影响。公元8世纪,赞普赤松德赞灭苯之时,卫藏地区的许多塞康被毁,许多苯教大师逃到了多康地区。从上述墨尔多神山的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一部分苯教大师逃到嘉绒地区,并把卫藏地区的塞康文化带到了此地。这些塞康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被改变为寺院。雍仲拉顶寺曾是嘉绒地区最大的寺院之一,是整个嘉绒十八土司的总寺院,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统领作用。雍仲拉顶寺在金川战役中被毁之后,嘉绒地区许多苯教寺庙都跟雍仲拉顶寺一样被强行改宗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另外一个较为重要的苯教寺庙就是金川县的昌都寺(![]() )①昌都寺,昌都为藏语
)①昌都寺,昌都为藏语![]() 或
或![]() 的音译,分别为高海、海上之意,寺庙坐落于山腰上,与一个小湖相邻。该寺全名昌都辛教宝洲(
的音译,分别为高海、海上之意,寺庙坐落于山腰上,与一个小湖相邻。该寺全名昌都辛教宝洲(![]() ),简称昌都寺,坐落于周山区撒瓦足乡三村,距金川县城西北36千米。据《苯教史纲要》载,“相传该寺院是由一位绰斯甲土司的兄弟丹贝坚赞于藏历饶迥开始前两年创建的,应该是1025年,但寺院所有的文献资料均被毁,无从考证”[11]。《绰斯甲土司世袭》一文认为,绰斯甲土司索南诺布(
),简称昌都寺,坐落于周山区撒瓦足乡三村,距金川县城西北36千米。据《苯教史纲要》载,“相传该寺院是由一位绰斯甲土司的兄弟丹贝坚赞于藏历饶迥开始前两年创建的,应该是1025年,但寺院所有的文献资料均被毁,无从考证”[11]。《绰斯甲土司世袭》一文认为,绰斯甲土司索南诺布(![]() )和拉章丹增诺布(
)和拉章丹增诺布(![]() )掌权时期创建了该寺②这里把昌都寺的藏文写成“
)掌权时期创建了该寺②这里把昌都寺的藏文写成“![]() ”,与“
”,与“![]() ”或
”或![]() ”稍有区别,但纯系藏文拼写差异,实为同一寺院。因该寺是绰斯甲土司所建,因此,在嘉绒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其地位、声望仅次于雍仲拉顶寺。“塞琼扎(
”稍有区别,但纯系藏文拼写差异,实为同一寺院。因该寺是绰斯甲土司所建,因此,在嘉绒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其地位、声望仅次于雍仲拉顶寺。“塞琼扎(![]() )之后裔分为族系传承(
)之后裔分为族系传承(![]() )和教法传承(
)和教法传承(![]() )两种,而苯教教法的传承世系中主要有照衮(
)两种,而苯教教法的传承世系中主要有照衮(![]() )、扎巴(
)、扎巴(![]() )、苏仓(
)、苏仓(![]() )、卡热合(
)、卡热合(![]() )、廓蚌(�U
)、廓蚌(�U![]() )等”。[12]因此,这些由琼氏后裔所建的寺院在传播苯教的活动中一直是中坚力量。
)等”。[12]因此,这些由琼氏后裔所建的寺院在传播苯教的活动中一直是中坚力量。
1751年,促浸土司绕丹郎卡杰布(![]()
![]() )邀请著名的苯教大师贡珠扎巴甲村宁波编写了苯教大藏经《甘珠尔》目录,取名为《深广雍仲苯教大藏经〈甘珠尔〉目录十万日光》(
)邀请著名的苯教大师贡珠扎巴甲村宁波编写了苯教大藏经《甘珠尔》目录,取名为《深广雍仲苯教大藏经〈甘珠尔〉目录十万日光》(![]()
![]()
![]() ),并出版了一套苯教木刻版《大藏经》。然而这套《大藏经》在金川战役中被毁。此后,绰钦土司根嘎诺布(
),并出版了一套苯教木刻版《大藏经》。然而这套《大藏经》在金川战役中被毁。此后,绰钦土司根嘎诺布(![]() )在残存的木刻板基础上补充雕刻,完成了第二部完整的苯教大藏经《甘珠尔》木刻版,同样在此后的第二次金川战役中被毁。尽管这两套木刻版苯教《大藏经》的完整版早已不存了,但在编辑、刻印、传播苯教文献中,琼氏后裔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残存的木刻板基础上补充雕刻,完成了第二部完整的苯教大藏经《甘珠尔》木刻版,同样在此后的第二次金川战役中被毁。尽管这两套木刻版苯教《大藏经》的完整版早已不存了,但在编辑、刻印、传播苯教文献中,琼氏后裔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嘉绒地区,琼氏后裔兴建了许多苯教寺院,仅仅在绰斯甲辖区内就有四十多座。虽然,其中大多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型寺院和苯教道场,但这些寺院在传播苯教、象雄文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杂丁青寺(![]() ),是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的一座苯教寺院,著名的苯教大师夏尔杂・扎西坚赞(
),是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的一座苯教寺院,著名的苯教大师夏尔杂・扎西坚赞(![]() )也曾因受到得道者琼帕察莫之后裔绰斯甲土司的邀请而到过嘉绒绰斯甲、巴底和革什扎等地弘传苯教教法[13]。在甘孜州新龙县瓦雀寺(
)也曾因受到得道者琼帕察莫之后裔绰斯甲土司的邀请而到过嘉绒绰斯甲、巴底和革什扎等地弘传苯教教法[13]。在甘孜州新龙县瓦雀寺(![]() )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苯教《大藏经》,共187部,分为四个部分。《经部》84部,《康钦部》73部,《密部》19部,其它杂卷11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文革中幸存的文物时,发现这部苯教《大藏经》竟然是我国藏族地区仅存的一部完整的苯教《大藏经》,属于孤本文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在刊印的各类版本的苯教《大藏经》均离不开这个母本。在这部苯教《大藏经》的抄写、校勘、运输以及在文革中的保护都离不开琼氏后裔的参与和努力。
)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苯教《大藏经》,共187部,分为四个部分。《经部》84部,《康钦部》73部,《密部》19部,其它杂卷11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文革中幸存的文物时,发现这部苯教《大藏经》竟然是我国藏族地区仅存的一部完整的苯教《大藏经》,属于孤本文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在刊印的各类版本的苯教《大藏经》均离不开这个母本。在这部苯教《大藏经》的抄写、校勘、运输以及在文革中的保护都离不开琼氏后裔的参与和努力。
四、东西女国的历史文化联系
关于历史上的“女国”这个称谓出现在汉文史籍当中。对汉文史籍的研究者来说,“对于隋唐时期青藏高原范围存在东、西两个女国,这一点学术界没有疑义”[14]。但是,不仅汉文史籍对两个女国都称呼“东女国”,而且两个女国的文化习俗的记载有大量的相同点,因此,对于两个女国确切的所指和地理位置,学术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关于两个女国的地理位置,学术界争议颇大。关于葱岭之南女国,有苏毗说、大羊同说、小羊同说等;对于川西高原女国,有金川说、昌都说、先在昌都后迁至金川说等多种。摘自石硕:《〈旧唐书・东女国传〉所记川西高原女国的史料篡乱及相关问题》,《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4页。
对“西女国”,即“葱岭之南女国”的历史记载,最早出现于《隋书・裴矩传》,该传引用裴矩所撰《西域图记》序言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除此之外,《隋书・西域传》中也列有“女国传”。任乃强先生在《隋唐之女国》一文中说到,《隋书・女国传》的叙述来源于裴矩的《西域图记》[15]。另外,唐初所撰《北史》的《西域传》中也有“女国传”,其文字与前文大体相同。这两个文献所记述的“女国”均为“葱岭之南”之女国,位于于阗南去三千里之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东女国也,……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道宣在《释迦方志》里记载到:“东西地长,即东女国,非印度摄,又即名大羊同国,东接土蕃,西接三波诃,北接于阗”[16]。除“葱岭之南”之女国以外,汉文史籍还记载另一个女国。《旧唐书・西南蛮传・东女国》记载到:“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按照地理位置的指向,该“东女国”确实与前者不同。因此,后面就出现了“东女国”与“西女国”这种说法,以此区别。但为什么两个地理位置相隔数千里的女国之风俗习惯大体相同呢?对此,学者们的说法各不相同②任乃强先生认为两个女国同俗。任乃强:《隋唐之女国》,载《任乃强民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山口瑞凤:《东女国和白兰》,《东洋学报》54卷第3号,第1-56页,该文中认为同俗为葱岭之南女国变迁至川西高原所致;石硕先生认为是史料篡乱导致了同俗的记载。石硕:《〈旧唐书・东女国传〉所记川西高原女国的史料篡乱及相关问题》,《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42-P148页。其实,笔者认为要是以藏文文献为基础,试图对比两个女国古今的文化和宗教,再来对照汉文史籍去理解的话,似乎能够对两个“女国”文化习俗大致相同的原因了解一二。
从它们的地理位置来看,“葱岭之南”女国为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而“川西高原”女国为今青藏高原东部嘉绒地区。《琼布世系金盒》等许多有关苯教以及琼氏家族的藏文文献一致地记载,琼氏家族取代扎氏成为象雄王国的主要氏族之一,之后,没落而东迁至今西藏昌都丁青地区,最后到达今嘉绒地区。随着琼氏家族的东迁,把苯教信仰和琼鸟崇拜等文化传到了青藏高原东部的嘉绒地区。除了口传史及文献记载以外,两个地方同样崇拜琼鸟、信仰苯教、语言有相同点等这些更为直观的证据可以证实,象雄文化从“葱岭之南”女国通过琼氏家族的东迁传到了“川西高原”女国。《释迦方志》所记“又即名大羊同国”似乎道出了真实情况。石硕先生也意识到这点之后,在“中国国际象雄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从碉楼称谓“邛笼”一词看象雄文化的东传及时间》的论文,认为象雄文化以及琼氏家族东迁的时间大约在东汉时期或者更早。对于“女国”这个称呼的起因,汉文史籍记载为“世以女为王,因以女为国”或“俗以女为王”。但笔者认为这些记述或观点很有可能是理解错误或理解不够准确而造成的。因为除了汉文史籍以外,藏文文献对这两个“女国”只字未提。要是当时真有这么两个“女国”与吐蕃相接的话,藏文历史绝对不会视而不见的。
以藏文为基础来研究“女国”这个称呼似乎更为有力。嘉绒地区有一座非常有名的神山叫做嘉姆墨尔多山(![]() ),这里的“嘉姆”指的是居住在这座神山上的苯教最重要的护法神斯贝嘉姆(
),这里的“嘉姆”指的是居住在这座神山上的苯教最重要的护法神斯贝嘉姆(![]() )①斯贝嘉莫的意思是世间女神,因此不能被翻译成女王。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女神”。嘉姆墨尔多神山是斯贝嘉姆女神的居所,所以,护法神斯贝嘉姆的居所嘉姆墨尔多神山周边的炎热的山谷就被称作东方嘉姆嚓瓦绒(
)①斯贝嘉莫的意思是世间女神,因此不能被翻译成女王。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女神”。嘉姆墨尔多神山是斯贝嘉姆女神的居所,所以,护法神斯贝嘉姆的居所嘉姆墨尔多神山周边的炎热的山谷就被称作东方嘉姆嚓瓦绒(![]() )②嘉莫,即女神;嚓瓦,即炎热;绒,即峡谷。因为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偏低地区的高山峡谷地带,气候比其他藏区炎热,故得名。“即以嘉姆墨尔多山为中心,四周方园千里之地的区域名,简单说就是墨尔多山周围的地区之意”[17]。对此藏族学者已经有明确的诠释[18]。藏文“东方嘉姆嚓瓦绒”,从字面上可译为“东方女神谷”,或“东方女王谷”。因此,汉文史籍中出现的“女国”很有可能是把藏语“斯贝嘉姆”或“嘉姆”理解为“以女为王”,而把这个“以女为王”的地域称之为“女国”。藏文“嘉姆”一词的确有“女王”之意,但当其作为嘉绒地区的地名出现的时候则与当地传统的苯教信仰有关,指的是护法神斯贝嘉姆,指的是女神,而没有汉文史籍所提到的“女王”之意。著名藏族学者毛尔盖⋅桑木丹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嘉姆嚓瓦绒的名字源于“嘉姆墨尔多”这座神山之名[19]。
)②嘉莫,即女神;嚓瓦,即炎热;绒,即峡谷。因为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偏低地区的高山峡谷地带,气候比其他藏区炎热,故得名。“即以嘉姆墨尔多山为中心,四周方园千里之地的区域名,简单说就是墨尔多山周围的地区之意”[17]。对此藏族学者已经有明确的诠释[18]。藏文“东方嘉姆嚓瓦绒”,从字面上可译为“东方女神谷”,或“东方女王谷”。因此,汉文史籍中出现的“女国”很有可能是把藏语“斯贝嘉姆”或“嘉姆”理解为“以女为王”,而把这个“以女为王”的地域称之为“女国”。藏文“嘉姆”一词的确有“女王”之意,但当其作为嘉绒地区的地名出现的时候则与当地传统的苯教信仰有关,指的是护法神斯贝嘉姆,指的是女神,而没有汉文史籍所提到的“女王”之意。著名藏族学者毛尔盖⋅桑木丹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嘉姆嚓瓦绒的名字源于“嘉姆墨尔多”这座神山之名[19]。
结 语
琼氏家族在古象雄崛起后逐渐成为最为重要的氏族之一,在象雄和吐蕃的历史进程中也十分重要。琼氏部落东迁对象雄文明的传承,尤其是苯教文化传播到青藏高原东部嘉绒地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扮演了文明传播者的角色。尤其是琼鸟信仰的东传,对嘉绒藏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东汉甚至更早的时期,原始苯教信仰就已经传到了嘉绒地区,其中,琼鸟信仰曾是当时苯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琼鸟,在早期嘉绒藏族文化中具有如此高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琼氏部落的人们认为他们是琼鸟的后裔,琼鸟就是他们的祖先。这种神鸟信仰和祖先崇拜的合二为一的现象,致使神鸟信仰在嘉绒藏族宗教文化中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延续性,使其成为嘉绒藏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象征符号。琼氏部落,起源于古代象雄的中心区域,因种种原因开始东迁,途径琼波(今那曲巴青和昌都丁青一带)等地而最终到达了嘉绒地区。据传,琼氏中“白琼”最早到达了嘉绒地区,因此,嘉绒藏族至今认为自己是“白琼”的直接后裔。琼部落与当地的土著人相结合,从而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嘉绒藏族。
关于古代“葱岭之南女国”和“川西高原女国”,也就是所谓“东女国”和“西女国”之间的关系,《隋书》《旧唐书》等都有过相关记述,其中也不乏几乎相同的内容。对此,有人认为是不同史料之间互相通用或改写所致,或者年代较近的史料中发生了互为混淆。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风俗如此相似是由于东迁所致。但是,东迁说受到了学界一些人的质疑,理由是:两“女国”相距太远,若发生过大的迁徙活动两地之间理应会留下种种过渡痕迹,然文献中未曾提及。依笔者之见,对东迁说的质疑乃是不熟悉相关藏文文献所致。事实上,琼氏部落从西部象雄迁徙至嘉绒的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非常多,对此不仅藏文文献有记载,而且琼波地区也有琼氏部落的后裔。过去属于琼波地区的巴青县现有三十多座苯教寺院,是我国藏区惟一一个只有苯教的县,而且琼鸟信仰也在那里非常盛行。如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西女国其实就是象雄,东女国就是嘉绒,所以,两地在碉楼、丧葬等方面多有文化上的相同之处。
如今,琼氏后人遍布几乎整个藏区。琼氏后人从阿里地区出发,途径那曲、昌都等地,最终到达了四川东部的嘉绒地区。也有一小部分到达更远的纳西族、普米族、摩梭人等地区落脚,并在那里开始传播苯教,留下了琼氏后人的印记。在琼氏家族东迁的历史进程中,建立“塞康”等宗教场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本文中提到的雍仲拉丁寺就是在之前的“促浸夏骁塞康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很多早期所建的“塞康”因种种原因未能延续至今,但在历史上对琼氏家族东迁和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选自: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P90-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