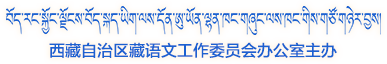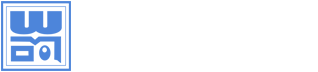汉藏互译中的藏区地名错写误译现象探析---以部分村名及景点作为案例阐述
punctuation'>
【摘要】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地名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符号,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深受时代背景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藏区地名汉藏互译中存在的一些被错写误译的案例,阐述地名错写误译现象对区域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与危机。故此,正确认识地名翻译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感,纠正并杜绝此类现象,从藏区地名汉藏互译中实现文化正确传递的重要性。
【关键字】汉藏互译;地名 错写误译
前言
西藏申扎尼阿木底旧石器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证明,早在3万年前就在青藏高原腹地有人类居住。[①]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单独孤立存在,都离不开邻边民族及国家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其中翻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藏族的翻译始于唐朝初期,在历时1300年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藏译人译著,汉藏两种文字的互译活动,促进了汉藏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交往与交融,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汉藏民族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团结。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我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汉藏翻译事业随之也有了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汉藏翻译事业机构的完善、专业培训及填充人员编制等一系列工作逐年优化,创造了汉藏翻译事业的一片蓝天。尤其是我区在中央的关怀和全国的支援下,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愈发频繁、愈显深入,使得藏区的翻译事业肩负着搭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任务。同时,面对不断纵深的文化融合与冲击,加之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知识领域凸显的信息量膨胀、知识碎片化,甚至信息真假难辨等问题也在翻译领域时有发生,西藏的翻译事业可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藏区地名错写误译现象即是近年来出现的此类问题之一,笔者作为一名汉藏翻译工作人员,针对藏区地名汉藏互译问题,提出几点拙见。
一、藏区地名汉藏互译中的错写误译现象案例分析
藏区的山山水水都有名字,都有它神奇的传说,每一个地方都谱写着古老藏民的智慧,藏区地名翻译分为藏汉、汉藏两种,其中汉藏翻译其实是转化最初的藏文原貌,而不是重新编译新的名字。藏区地名汉藏翻译和藏汉翻译不同,藏汉翻译一般都是音译为主,主要讲究汉藏普通话为标准,发音对比的同时选择不带歧义的字词规范后使用,如:ལྷ་ས། -拉萨、 རིན་སྤུངས།། -仁布,དིང་རི་-定日,但也有长时间的惯用约定俗成的,如:གྲོ་མོ།-亚东、དར་མདོ།-康定等。但是藏区地名汉藏翻译必须按照“约定俗成”或者“名从主人”的原则。上个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不断高涨,给汉藏翻译事业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汉藏翻译人才和重要译著。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个时期出现的误译现象,导致了今天很多的汉藏地名翻译不规范的问题。然而,当下的翻译现状也不容乐观。年轻译人既不了解藏族历史文化,又对翻译工作的严谨性不强,在藏区地名汉藏翻译中主要使用音译为主的译法技巧,导致了大量地名拼写错误,毁掉了原有的名字及文化。下面从三个方面的案例分析西藏地名汉藏、藏汉翻译中的错写误译现象。
(一)实地标牌中的错写误译现象分析
为更好地阐述藏区地名错写误译现象,笔者对西藏仁布县为主的其他部分地区作了调研。(1)西藏日喀则仁布县切娃乡奴达村的写法而言,“努达村”汉文的写法已经非常规范,一直使用“努达”很少有人出错。但在各级的汉文材料翻译成藏文的时候,努达村的地名被写成“ནུབ་མདའ་གྲོང་ཚོ་”其意思为西面山谷下部村庄,如今村委会的门牌也挂有“ནུབ་མདའ་གྲོང་ཚོ་”,实际上现在的努达村是吐蕃第一任国王聂赤赞普时期的西藏王室六大氏族中的努卜氏人民居住地方的下部,该氏族的藏文写法是“གནུབས་”,地名也是氏族的名字而得来,因此,正确写法应该是“གནུབས་མདའ་གྲོང་ཚོ་”。(2)后藏绰普寺地名路标上写有“ཁྲུའུ་ཕུ་དགོན་”,该寺的汉译名字更为离谱,写成“楚布寺”,完全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主庙名字相同。绰普寺是公元十三世纪绰普译师强白所创建,该寺的名字也是创建者的人名而得来,绰普译师强白的藏文写法是ཁྲོ་ཕུ་ལོ་ཙྰ་བ་བྱམས་དཔལ།因此,该寺的其正确写法是“ཁྲོ་ཕུ་དགོན་”。(3)坐落在西藏亚东县堆纳乡境内的多庆措(རྡོ་ཆེན་མཚོ་)其名字是由于该湖泊位于堆纳乡多庆一带而得名,汉文“多庆措”仅仅是藏文的音译词语,并无其他意思,但近年来大力开发西藏旅游事业,当地为吸引游客,把沿用已久的汉文湖名改为“多情措”并立有石碑、建设旅游观光点,误导游客正确了解西藏文化,这种相关部门的不负责任行为,既是对藏文化的正确认识带来极大的影响,也是因崇尚藏文化而旅行到西藏的游客来讲,也是极大的不尊重。(4)坐落在西藏阿里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境内的“措木昂拉”现取名为“班公湖”,事实上汉文的“班公湖”和藏文的མཚོ་མོ་ངང་ལྷ།音与译俩方面没有任何关联,也不是约定俗成的地方名字。据当地老人介绍在日土县日土村热角境内有一座小湖泊,叫སྤང་སྒུར་མཚོ།(邦贡措),“措木昂拉”与“邦贡措”自古是两座湖泊,但如今当地把“措木昂拉”的名汉文名字写有“班公湖”并在湖边立石碑名字,这个离奇古怪的命名,毁掉了两个湖泊的真实历史。
(二)汉藏地名词典中的错写误译现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翻译前辈学的辛勤努力下,藏区翻译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版了《汉藏大辞典》为主的很多翻译工具书,这些书籍为后来的翻译工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翻译行业的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不同版本的藏区地名汉藏词典陆续问世,但由于种种因素,本因一地一名的地名词典,在不同的编审及不同的出版社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写法,这使广大翻译界人员参考使用翻译工具书带来很大的困难,这种不统一的地名词典的推广不仅对翻译界没起到作用,而且对历史地名文化遭受极大破坏。(1)仁布县仁布乡རི་ལུང་སྦུག而言,在中国藏学中心出版的《西藏地名》中写有“日龙普--རི་ལུང་སྦུག”[②],在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行政村名及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中写有“日朗布--རི་གླང་སྦུག”[③],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藏对照新词术语》中写有“日龙布--རི་ལུང་སྦུག”[④];(2)西藏仁布县“江嘎”达村,在《汉藏对照新词术语》中写有“江嘎--རྒྱང་མཁར།”[⑤],在在中国藏学中心出版的《西藏地名》中写有“江嘎--རྒྱལ་མཁར། ”[⑥],在《西藏自治区行政村名及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中写有“杰嘎--རྒྱལ་མགར།”[⑦]。(3)西藏山南市隆子县“杂日”乡,其中的杂日是该地区一座著名圣山及山脚下地区的名字,十二世纪末,藏传佛教噶举派藏巴甲热也协多吉始说此山为佛教密宗胜乐金刚圣地。该山名的正确写法在《汉藏大辞典》、《新编正字》、《学生藏文词典》上都写有“ཙ་རི་”,根据当地人的介绍这个写法是自古传下来,并在长期的生活中一直惯用,因此杂日乡的正确写法应该是“ཙ་རི་ཤང་”但以上三个词典中都写有“རྩ་རི་ཤང་”。类似这种,不同汉藏对照词典中地名不统一的现象极为严重,但目前西藏的汉藏互译人广泛使用这些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写法,出现了一地多名,使人无法正确了解该地真实文化。
(三)地图中的汉藏地名错写误译现象
地图作为再现客观区域的形象符号模型,是信息传输工具之一。编图者须充分掌握原始信息,研究制图对象,结合用图要求,合理使用地图语言,将信息准确地传递给用图者。
藏民祖先在这片广阔富饶的青藏高原创造了十分辉煌的人类文明,西藏独特的人文风情,吸引着世界各地游客。一到旅游旺季地图的销量大、使用量广,西藏地图不仅在各大书店销售,而且在拉萨老城区为主要地段的旅游商行及户外旅游景区附近均有销售,但地图中所描绘的地名出现了不一样的用字,给地图使用者带来极大不便,甚至同一个地图上的同一个地名出现不一样的写法。如:仁布县切娃乡རྒྱལ་གཞོང་།在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图册》中写有“杰雄”[⑧],在星球地图出版社(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图集》中写有“借雄”[⑨];另外,在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图册》中把仁布县ཁུ་ལུང་མདའ།和ཁུ་ལུང་ཕུ།的汉文用字不一,写有“库龙达、苦龙普”[⑩],地图使用者误认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库龙一带的上部与下部;还有在星球地图出版社(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图集》中把仁布县姆乡的སྨོན་སྟོད།一词在地图上出现了两次,事实就是一个地方,但汉文的名字写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字样“姆堆和木堆”[11],这样使很多人自然误认为是两个不同地方。
以上行政村名、寺庙路标、旅游景点案例中既有藏汉错译,也有汉藏错译。这里特别说明的是藏区地名从汉文翻译成藏文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来看,“汉藏地名误译”现象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交往与交融,普通话和汉字作为我国的官方语言和文字,很多藏区的地名已经在汉文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地名术语,当翻译人员遇到各个领域的翻译材料时,牵扯到很多藏区地名汉藏翻译,实际上藏区地名从汉文翻译到藏文,这本来是一个循环性的翻译工作。一个地名其最初就是藏文,译者无需针对汉文编译新的名字。但由于新生代翻译人员没有较强的翻译理论素养和其它领域的知识,出现大量的“汉藏地名错译”现象。导致了不仅翻译错误,而且对区域文化,乃至藏文化带来极大的影响。藏区地名的汉藏翻译,这个译出和译回出现的问题,在翻译界司空见惯,已不再是个稀奇的话题。但从一般有点藏文常识的人看来,始终觉得所犯错误低级可笑,且不容忽视。这样的误译现象事实上也普遍存在。
众所周知,地名翻译音译为主要方法,必须按照“约定俗成”原则,这是国际地名翻译惯例。关于这个理论体系方面,汉藏互译中也形成了较多的理论书籍。在《汉藏互译教程》中指明历史地名的译法和历史人名的译法一样,也应以“约定俗成”为主要原则,尽量少用新的音译。[12]在《汉藏语法比较与翻译》中也强调地名翻译要做到“约定俗成”,有的词语的拼写习用已久,固定成型的,不再改动或新造。[13]另外在《翻译理论新探》中写到“མི་མིང་ས་དང་དོན་མང་མིང་། སོར་འཇོག་སྒྲ་དང་འདྲེས་མར་སྒྱུར། མི་མིང་མེས་པོའི་བྱེད་པོར་བསྟུན། ས་མིང་སྔ་མའི་སྲོལ་ལྟར་བསྒྱུར།”[14]其意思是地名翻译要在音译的基础上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事实上约定俗成的原则就是充分尊重祖先用智慧取下的名字,不能随意更改用字,要充分尊重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正确写法。地名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我们没有认真分析研究该地名最初的来源,随便音译或者用其他文字的现象,毁掉了正确的历史文化、切断了一项重要的藏族文明发展研究线索。地名不因某种的需求而变更名字及用字,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是对我国灿烂文化的尊重,是对祖先的尊重。
二、藏区地名汉藏互译中的错写误译现象原因分析
在新时期的地名汉藏互译过程中出现类似的错写误译现象,其主要原因归根为四大类。
(一)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高的影响
地名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能够折射出历史痕迹和社会变迁。从文化学角度看,它既有一个时代文化特征,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彰显一定时期的历史信息,对一个地域的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现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谭其骧先生曾说,“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按照谭其骧先生的说法老地名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因此,出版社、编审人员、地名翻译人员都应当正确认识地名工作的重要性,本着对区域文化负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负责、本着对子孙后代的正确认知负责的原则,认真研究地名历史的真实来源,要用词与意相符,通过实地调研、文献参考、相关部门相互沟等方式做到一地一名、汉藏字词统一。应严厉杜绝文化项目中应付式工程的开发,杜绝不负责任的译人译著。
(二)历史时代背景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藏区很多政治、经济、文化要地都有它的汉文名字,比如:བོད། -吐蕃、乌斯藏、卫藏后改定为西藏;ལྷ་ས། 逻些(逻婆)、吉雪、在明代西藏地方略图上也有喇撒[15]的写法、拉萨等。但由于在较长的时间里藏文的读音变化大,古今地名译法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西藏地名是后来产生的名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和平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西藏的历史画卷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云、贵、川解放后,十八军进军西藏,军队在进藏工作中由于对西藏的区情民风把握相对匮乏等因素,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地名工作也不例外。解放初期,一是进藏工作的迫切需求;二是我国没有形成普通话规定;三是汉藏双方主要用自己的方言沟通、记录等原因,遗留下了很多藏汉地名翻译不标准的现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全中国,西藏各个领域事业迎来的大好时机,汉藏翻译事业也在前辈们的努力下,为今天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地名翻译出错现象始终没有随机遇得到改善。如今,信息技术腾飞、已是互联网云技术时代,再去改变近四十年前的地名错误,似乎遥不可及,但通过这些问题,给我们未来的汉藏互译工作留下许多经验和思考。
(三)藏译汉时的错写误译现象影响
如上所述,新时期的汉藏互译中经常出现藏区地名汉藏翻译问题,年轻的汉藏双语翻译队伍很难胜任这项工作,其主要原因地名文化牵扯面广,地名的书写并非仅名字的代表符号而已,更多的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精神杰作,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藏区地名藏汉翻译主要以音译为主,也有个别约定俗成的惯例写法,但这种译法极少数。藏汉地名翻译方面1982年9月国家测绘局和总参谋部测绘局联合颁发了《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拉萨话)地名音译规则》(测绘出版社)1986,其中第二条 音译时,一般情况下(如旧地名、历史人名和全藏区的同性的事务名称等),藏语以拉萨话读音为准,汉语以普通话读音为准;特殊情况下(如新地名、现代人民和其他特有的事务名称等),藏语也可以各大方言有代表性的语音为准,汉语也可以该地区通行的汉语言语音为准。[16]但以往藏区地名藏汉翻译中存在很多读音不标准的现象,导致今天藏区地名汉藏翻译中出现错译现象。如:仁布县切娃乡普纳村(ཕུ་སྣ་གྲོང་ཚོ་)[17],这是典型的藏汉、汉藏地名译出译回中出现的错译现象。该地区曾经空无一人,是一片沙滩,直到2004年开始建设,并把切娃乡人民政府搬迁到此地,如今是仁布县较发达的小城镇。当地居民中自古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曲龙[18]一带变成七户人家,普纳一带有人住户的时候是世界末日”,意思是普纳一带是不可能有人住,是非常不吉祥的地方。尽管这个说法似乎不太符合科学,但民间传说作为重要的人类学研究资料来源,也有它的参考价值。因此,该地名的正确写法是“འཕོས་ནག” [pʰø¹¹naˀ⁵³],其意为不可搬迁之地,或者搬迁后万事不顺之地。这个写法既发音准确又意思到位。“འཕོས་ནག”的读音完全符合群众对该地名平时的发音。在藏汉翻译中འཕོས་ནག 音译成“普纳”似乎问题不大,因为汉藏两种语言在声韵调三方面完全相同的音节毕竟还是很少,多数在普通话的标准下,做到尽量接近,但是已规范的藏文名字ཕུ་སྣ་[pʰu¹¹na⁵⁵]一词源于错误的汉文名字“普纳”的音译。还有,仁布县查巴乡吴美村(འུ་སྨི་གྲོང་ཚོ་)[19]的藏汉地名写法均为错误,该村名的正确写法应该是ངུར་སྨྲིག་[ŋur¹³miˀ⁵³]གྲོང་ཚོ། 这是自古已有的名字,在热・益西桑格撰写的《热译师传》中记载到“དེ་ནས་ལོ་ཙྰ་བ་ཀུན་དགའ་རྡོ་རྗེ་རང་ཡུལ་དུ་བྱོན་ནས་བླ་མ་སྤྱན་འདྲེན་པའི་གྲབས་གཤོམ་ཆེར་མཛད། བླ་མ་དཔོན་སློབ་རྣམས་རོང་ངུར་སྨྲིག་ནས་གདན་འདྲེན་པ་བྱུང་བས་དེར་གཤེགས།”[20]ཡང་“རྟེན་གསུམ་སྤྱི་དང་ཁྱད་པར་ངུར་སྨྲིག་སྒྲོལ་མ་ལྷ་ཁང་ལ་སྙན་དར་སྒྲོན། ཞལ་གསེར། དཀར་མེ་སོགས་མཆོད་པ་རྒྱ་ཆར་མཛད་པའི་ཚེ་སྒྲོལ་མའི་ཕྱལ་མཐིལ་ནས་བདུད་རྩི་འོ་མ་འདྲ་བ་ལན་གསུམ་བབས།”[21]这两句的大致意思为热译师被受僧众的邀请后前往吴米一带举行盛大的宗教法事。热译师是出生在十一世纪(1016-1077),由此可断ངུར་སྨྲིག་一词是个古老的名字,另外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也有记载,说明十七世纪仍然使用ངུར་སྨྲིག་,如今广泛使用并已规范成型的汉语“吴米”一词多半是来自于当地群众的口语འུག་མིག [ɦuˀ¹³miˀ⁵³],尽管在藏区地名翻译中普遍存在类似这种现象,如:བྲག་རི་ཁུག-巴尔库,བྲག་ཡིབ།-巴宜,但巴尔库和巴宜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仅在语言的变化中形成,藏文的写法没有变动。再对以下几个地名的译出和译回做个比较,在2012年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中写有“མུན་གྲོང་ཚོ།-明村 、ཁུ་ལུང་མདའ།-库隆达村、ཡུལ་ལྷ་གྲོང་ཚོ་། -玉拉村”[22],在2016年出版的《西藏自治区行政村民系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中又写有“明村―མིང་གྲོང་ཚོ། 、库隆达―ཁུག་ལུང་མདའ་གྲོང་ཚོ།、玉拉村―གཡུལ་ལྷ་གྲོང་ཚོ།”[23],这两本地名词典中,以上几个地点的汉文字都是一样,但藏文名字大有变化。这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藏汉(译出)后已形成的汉文地名明村、库隆达、玉拉等,在汉藏(译回)过程中直接做了音译མིང་གྲོང་ཚོ། ཁུག་ལུང་མདའ་གྲོང་ཚོ། གཡུལ་ལྷ་གྲོང་ཚོ།,而没有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尊重原来的写法,出现了这些错误的藏文写法,导致了原来的藏文名字彻底丢掉,毁掉了该地区的正确人文历史,地名文化变的有名无实。将来还有可能产生其他更离谱的错写现象,就如当年错译的林芝八一一样(如:བྲག་ཡིབ།--八一--བརྒྱད་གཅིག)。
(四)翻译人员文化素养不高的影响
翻译是把有一种语言组成的材料所表达的意义(内容)用另外一种语言组成的材料表达出来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运用语文的活动,也是一种技术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脑力劳动。翻译不仅是文字的转化工作,它更多的是文化交流的工作。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两种及两种以上语言文字的功底,还需要其他多方面的文化素养,这样才能把原文的意思很好的表达出来。但是,目前藏区年轻一代翻译人员把汉藏互译工作仅仅视为查词典完成的文字转化工作,不去学习翻译理论及牵扯翻译领域的其他知识,导致了译文不通不顺,甚至译文内容违背原文。
人类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翻译理论,就对藏族而言自吐蕃时期就有了《声明学要领二卷》,国内有严复的“信、达、雅”,黄药眠的“透、化、风”等,这些翻译理论很好的阐述了翻译的技巧和方法,但是很多译人从不去学习,使译文既不符合汉藏文法又用字生硬,显得十分难懂。同时翻译需要精通翻译原文所涉及的专业学科知识和有关知识,这样才能掌握语言的规律、修辞特点、表达方式、感情色彩等。在《汉藏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关于翻译人员具备的条件方面概括为:一是精通两种文言文字;二是深入了解翻译理论;三是需要钻研多方知识;四是需要保持勤奋。[24]。译人的翻译面广,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量,就会出现大量的错译现象。如:仁布县切娃乡的努达村(གནུབས་མདའ་གྲོང་ཚོ་),从历史角度来讲,如果你不知道该地带是古代藏族努卜氏族的主要居住地点,很可能错译使用其他词语;从宗教角度讲,藏族人文地志中的宗教术语,如果你分不清苯、佛术语,也有可能错译,如སྟོན་པ།苯教译祖师、佛教译释迦牟尼;从文物角度讲,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墓葬方面一律不能译为བང་སོ། ,“བང་སོ།”是封土墓,其土堆垒起略显突形。墓葬译དུར། 墓葬室或者墓葬洞译དུར་ཁུང་། དུར་ཁང་། སྤུར་ཁང་། ;在文学角度讲,在汉文古诗翻译方面不仅把诗歌的内容吃透,而且要把作者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意识都要理解透,如: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到底指睡床、井沿、坐凳?所以不能一贯翻译成མལ་ཁྲི།,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充分的认识到翻译不仅是文字的转化工作,它所涉及的知识面广,我们只有掌握各个领域相关知识,才能译出理想的译文。显然,地名汉藏互译中的错写误译现象也是译者没有相关的知识文化水平所造成结果。
结语
综上所述,汉藏互译中的地名翻译不仅是翻译问题,更是继承和发扬该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人员不负责任的地名错写误译现象,将会切断一项重要的人类文明史研究线索,使中华文化之奇葩的藏文化研究遭到损失。我们应重视“汉藏地名错写误译”现象带来的种种问题,从中对当前的地名翻译有所危机感,清醒认识西藏地名翻译事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要提高地名文化保护意识,将原有的老地名挖掘、传承下去。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地名错误问题,笔者认为,一是政府应牵头开展实地地名文化研究,对地名工作进行系统梳理和资料收集;二是应成立一个由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专家组成的地名审核组,对新的地名进行讨论与审查;三是重大地名改变应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把命名工作做得更透明、更科学;四是藏区干群齐抓共管、上下联动,避免地名命名工作中的随意性、盲目性;五是做好已形成的新地名广告宣传工作,强化地名标志的设置及政府文件中的大力使用等。同时,在藏区翻译工作上政府应当加强汉藏互译队伍的建设、严谨翻译人员的翻译工作态度,提高其理论水平,加大力度对汉藏互译人员专业培训,扩招翻译专业人员,增设汉藏互译专业岗位等工作也显得极为重要。从而使翻译界进一步将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入农牧区,发挥其在政治、政策及其他领域的宣传桥梁作用;同时为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也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入围项目之三:西藏尼阿木旧石器遗址》中国文物报社2016.3.16日。
[②]武振华 西藏地名 [M]中国藏学中心出版,2007:417
[③]李万瑛 达哇才让 [M]西藏自治区行政村名及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 p607
[④]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M]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 西藏人民出版社 P 182
[⑤]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M]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 西藏人民出版社编 P 182
[⑦]李万瑛、达哇才让 [M]西藏自治区行政村名及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 p607
[⑨][M]西藏自治区地图集 星球地图出版社(国家一级出版社)p128
[11][M]西藏自治区地图集 星球地图出版社(国家一级出版社)p128
[12]周季文、傅同和 [M]汉藏互译教程 民族出版社 P266
[13]拉都 [M]汉藏语法比较与翻译 四川民族出版社P96
[15][M]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史料选辑)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p86
[16]周寄文 傅同和[M]汉藏翻译教程 民族出版社 p272
[17]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M] 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 西藏人民出版社 p181
[18]曲龙是离普纳村近五公里左右的奴达村的一个自然组,公元十三世纪初释迦室利受戒弟子乌则索南创建的曲龙寺所在地。
[19]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 [M]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 西藏人民出版社 p181
[20]热・益西桑格 [M]热译师传 青海民族出版社P188
[21]热・益西桑格 [M]热译师传 青海民族出版社P189
[22]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M]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 西藏人民出版社 p181-p182
[23]李万瑛、达哇才让[M] 西藏自治区行政村民系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 民族出版社p606-p607